阅读:0
听报道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6期
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
时间:2017年3月9日
“外地人”歧视为何根深蒂固?
新京报:大城市的“外地人”歧视由来已久,算不上是一个新话题。但近年来频频在社交网络上涌现的歧视,包括前段时间的“北京地铁男子骂‘外地鸡’”事件,仍然令人觉得很诧异:一是歧视不仅是当地人对外地人,还有一些外地人对其它外地人;二是歧视在很年轻甚至学生身上已经存在。这种观念,何以根深蒂固?
陆铭:从世界普遍性上讲,人类的天性,就比较倾向于跟相似特征的人相处,如果是跟不同身份、肤色或种族的人相处,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问题,心理学研究上也比较好解释。
但在中国要加一层,即人们没有一个很强的“国民”或“公民权”观念。在国家内部,有些权利是属于公民权利,应该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得到保障和尊重,但我们的教育理念缺这个东西。比如说在美国,如果对少数族裔有歧视,心里想想可以,但不能公开说。到了中国,就变成可以说的事了。我们需要一种公民教育,公开表达歧视——不管是民族、性别,还是地缘的歧视——都是非法的。回到外地人歧视这件事上,还同时涉及到其它问题,比如户籍跟实际的利益挂钩,再加上大家也不明白,城市的很多问题跟人多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从人们的感受来讲,好像很多问题都是人多导致的,比如交通拥堵。拥堵、污染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都很到了很好的治理,中国要多学习。
新京报:歧视本身即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外地人”歧视只是其中一种。除了刚才说的公开表达对“外地人”歧视,还有被制度化的歧视,比如户籍之下的城市福利、公共服务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外地人也常被作为是大城市病的来源。外地人和城市发展是何种关系?
陆铭:城市拥有大量移民,恰恰是有活力的来源,提供城市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大量的实证研究已表明,平均而言,他们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要比本地居民更强。当一个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收入高的阶层对服务的需求就提升,这就是“技能互补性”:越是收入高,就可能越是经常到外面吃饭,越是需要保姆,所有这些带来的都是对低技能者的需求。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如果不让低技能劳动者来,成本就上升,反过来讲,就减少对人才的吸引力。
中国大城市的期望寿命比较长,但全国退休年龄又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大城市的养老负担是很重的,外地人就业是在帮着本地人养老。如果离开这部分人,一个城市的养老都成问题,越是大城市,问题越是严重。
此外,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没有市民权这个概念的,citizen不是市民,是公民。在我的国家,我到哪里就业,是公民权之一,我在哪就业、在哪纳税,就在哪有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这是国际惯例。但因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我们目前没有做到,但至少得往这个方向上去。
新京报:刚才说到了两种歧视,一是个人层面的普遍性歧视,二是制度层面的公共政策歧视。如果要克服个人的歧视,实际上涉及到观念甚至价值观的改变,很难说可以让每个人都没有歧视,但我们仍在倡导改善公共政策,使之走向正义平等。
陆铭:在个人价值观层面,多元化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但在公共政策和社会价值观形成上,要强调公正和平等。
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公正和平等甚至通过逆向歧视来实现。很多资源的分配是按收入来,所以在制度上要把资源分配倾向收入、种族或身体维度上的弱势群体。个人价值观,可能存在一些“我就是看不起低收入的人”,但在社会价值构建上要反过来。我们还差得很远,很多制度设计,不是逆向而是正向歧视,比如说户籍的积分制,加入教育标准,相当于优先给高教育者获取本地公共服务的机会。
历史上的城乡不平等
新京报:相当数量的“外地人”是指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者,或者说移民者,有的能定居,有的则不能。前三十年,包括改革开放早期,城市优先于农村的发展关系,使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倾向于城市,而农村是被动付出的地位。这些历史遗产对今天的城市发展意味着什么?
陆铭:从历史看,制度的产生是有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的逻辑之下,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在城市积累资本发展重化工业,就需要把职工的工资压低,但为了职工没有意见,又要提供许多免费的服务,也就是单位制。同时,在城市里发展了大量的工业,但创造不了太多就业,如果放开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进城,提供不了就业岗位。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大不一样了。第一,刚才讲的历史原因不见了。第二,我们从城市解决不了就业,转向了劳动力短缺。第三,经济结构不一样了,当年是农业社会,现在90%的GDP在工业和制造业。随着中国的发展阶段即将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恰恰是在城市。发达程度在提高,城市化率不提高,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在接近一个发达国家,但在价值层面上,还没有做好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备。

新京报:城市约等于“单位”,从生老病死、教育到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包干。农村对城市的想象就是“吃国家粮”,高人一等。
陆铭:现在都没有这些了,但还根深蒂固的,是原来遗留在我们脑子的东西。政策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是在制约我们的经济和城市发展。经济的发展被限制了,社会的公正问题没有被解决。
“公”的边界打破到户籍这一层就停下来了
新京报:我们来看摆在面前的问题,既有个人层面的“外地人”歧视和偏见,也有公共政策的,更令人困扰的是,就目前而言,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你说的“逆向歧视”。问题的解决难点是什么?
陆铭:以我多年的讨论和与公众的接触来讲,第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很多问题讲清楚,而当前的舆论环境也不利于把问题讲清楚,因为大家不理性,宁愿相信直觉。直觉容易看啊,比如把交通归结于人多,这很符合直觉。但如果要讲一番道理,人们接受不了。我写《大国大城》的原因是,许多人原来就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一直只是传统的印象,就觉得“大城市”不好。
第二,我们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秩序,到公共参与,再到最基本的公民权的概念,没有仔细讨论过。一个人在哪工作,就在哪交税,就在哪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应该通过法律来保障。一个公民有选择在哪就业和居住的权利,应该被写入《宪法》。如果跟你讲道理,还是改变不了你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还有法律和宪法来作为保障。1975年之前的《宪法》里有自由迁徙和居住是公民权利这一条,因计划经济逻辑被去掉了,但现在写入的时机成熟了。1982年便有人大代表提出,现在又三十年过去了。
新京报:通过户籍及其附带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子女教育限制人口迁移,在当下仍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策倾向,是否能得到改变?
陆铭:我经常接触不同层面的政府官员,我真心认为,如果把道理将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听,他们听明白,也是愿意改变的。现在的结果是因为,许多的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想的是对的,比如根深蒂固认为北京上海就是太大了,就该限制人口。
我一个同事的丈夫是政府官员,她把我的书放在书柜,她丈夫此前也认为上海就该控制人口,但现在把书拿出来看,他也改变了看法。上海交大承接上海局级干部培训,我上完课,大家也都赞同,尽管也少数根深蒂固认为原来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以改变,但需要理智一点,舆论环境再宽松一点,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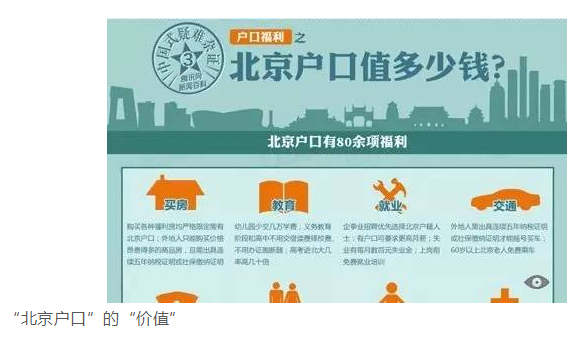
新京报:民众的意见亦是重要的一环。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比如裴宜理,他们提出中国的“权利”观念跟西方不一样,历来追求的是生存权、社会福利权,而不是平等与自由的权利。如果照此说来,民众在推动公共政策改变方面的现实需求似乎不大。是这样吗?
陆铭:这种看法已跟不上中国的现实了,但也不是说她就错了。从历史传统上讲是这样,我们的“公”或公共概念,不是现代的,而是家庭和家族的概念,其实可以说,只是一个更大的“私”。我们不是对平等和自由没有追求,而是说这种追求是被扭曲的。比如教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论点,“如果现在让外来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就对城市里的人不公平”,大家也谈“公平”,但却把特权的维持理解成公平。
再说自由,涉及到个人就讲自由,但涉及到别人,就不讲自由了。对公平和自由,对权利的追求,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现在都有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权利讨论范围是什么。家庭和家族作为“公”的边界被打破了,打破到户籍这一层就停下来了。我再讲一个更鲜活的例子,如果让上海人或北京人捐款到中国穷困山区的地方建学校,他们是很愿意的,很多人富裕了愿意做,但如果让他们把孩子带到北京或上海来上学,就不干了。现在的公共政策的逻辑也是这样,支持到农村或到落后山区援建学校,但不支持外地人的孩子来大城市上学。
城市公共政策需要改革
新京报:通过扶持或援建,相较于从前,的确改变了城乡的一些资源分配,但从你的《大国大城》中可看到,你不认为这是根本之策,保障人口自由平等流动才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陆铭: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现在做的都不太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道理很简单,一个现代国家城市化率都是70%、80%或更高。当然了,仍有人是待在农村,的确需要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也要保障那些选择离开老家进城的人的权利。不能说一些人进城了,在老家帮忙建了学校,就不用保障他们在城市的权利。同样的逻辑可以运用到小城市和大城市,比如有人不愿意放弃小城市的大房子和生活环境,对于这些人来讲,需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对于愿意离开的,是不是该保障他们的权利?不能因一部分的选择,就不尊重另外一部分人的选择。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